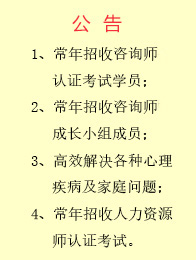明悦心理
1 、从自我谈起
自我一词,一般并不用于口语,而是代词“我”名词化的书面形式,当然同时也适应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英语self是个名词,故用作术语无需加工。这是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的。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术语中,有必要将self区别于Ego(因二者都译成自我)。前者是描述性的术语,后者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术语。 “Ego”是个拉丁词,相当于英语的“I”。弗洛伊德在构建他的理论时把一般人所说的自我分成三部分,即“本我(id)”、 “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这是弗洛伊德研究神经症所得出的观点。其实,本我若完全是无意识的即生物学的,严格地说,并不在心理学的论域之内,弗洛伊德用“它”(id)表示也有这个意思,而社会规范在一般人心里所反映的观念和情感是整合在自我之中的,所以没有必要分出一个超我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精神分析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有些现象的描述也采用了ego这个词,如同性恋有自我协调的(ego-syntonic)和自我不协调的(ego-dyntonic)。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妄想都是自我协调的,强迫观念都是自我不协调的。
自我与人格之关系的观点,过去相当混乱,现在二者的区别比较明朗化:人格一般是从行为的视角来描述一个人的整体,而自我所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他的心理的觉察和体验。
在弗洛伊德的晚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出现了对心理发育过程的研究重点从本我向自我的转移,即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学派。这一学派除了继续强调自我的动力性(psychodynamic,即对动机、目的之强调)外,还特别重视自我与客体的关系,以及文化对成长的塑造,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心理学对自我的重视和研究是从W. James开始的。
自我是一个多维概念,可以从它的发育成长、功能、内容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描述。
一位2岁还差2个月的男孩的言语显示他的占有观念已很明确而强烈。“宝宝的被被”(指他睡觉用的棉被),“宝宝的篮篮”(指他睡觉的摇篮),“宝宝的毛毛”(指他的玩具狗)等等,经常挂在嘴边,并且别人如果表示要拿走(故意逗他)他的这些东西,他便表现强烈的反抗。有一次,他的姨(十几岁的姑娘他称之为“芳姨”)抱他出外,看见一头牛,牛突然叫了一声,这男孩吃了一惊。回家后他便有下列一连串的描述:“芳姨抱,看见牛,牛怕,宝宝怕,芳姨怕,妈妈怕,姥姥怕。”这话表明,男孩的主体意识尚未形成,他还处于物我不分、浑然一体的状态。从这两段话可以概括出:占有的我先于体验的我。换言之,先出现“我有”观念,后出现“我在”。一般地说,到3岁左右,儿童才会说“我”,才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才有清晰的“我在”体验。反思是自我发展高级阶段的成就,大概在少年期的开始。此时,自我能超出自我之外来反现自我,或者说将自我客观化(作为对象)加以考察。也可以说,此时自我可以一分为二:主体的自我和客体的我。
佛教认为,生老病死是苦,并不尽然。猪也有生老病死,但猪似乎并无人之苦。即使明天将被屠宰,猪今天仍吃得很饱,睡得安稳,跟昨天完全一样--猪没有明天。由此,可以说人之苦是对明天预测或预知所致之苦。穿透未来时间的能力是自我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是智慧之光,也是痛苦之源。
也许,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产物就是英文所谓insight,汉语译作洞察、领悟、自知力等。
以上是笔者就自我发育成长这个维度所作的一种描述。临床观察表明,在精神障碍的病程中,较高级阶段的能力总是较容易受损害,也较早出现损害。精神病人的特点之一是自知力严重受损,现实检验能力(reality testing)严重受损。不少这类病人对个别症状能够反思,如轻躁狂病人,有时承认自己话太多不正常,精神分裂症病人有时知道幻听是病态,但他们对精神障碍总的说却没有自制力。痴呆与非痴呆的记忆,智力减退的区别在于反思能力缺乏。老年性痴呆在发病的较早阶段便丧失了对自我能力减退的反思,而脑血管病人和一般高龄老人即便记忆功能受损相当严重,他们仍保持着反思能力,通常苦恼地觉察到自己脑功能的减退。因此,在记忆测验完毕时,必须询问受试者:您感觉现在的记忆跟过去相比较有没有变化或不同?这样一问,对诊断大有帮助。
癫痫性精神病(这里精神病系现象学派的概念,即它是一个过程,只能用原因说明的结果,而不是症状与人格、生活经历等之间存在有意义的联系,而可以理解为反应或发展)很特殊。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个突出的例子。他长时期保持着很高的智慧(创作长篇小说便是明证),但他常有很特殊的发作,在这些发作时,他的存在体验发生了严重紊乱:我变得完全不一样,时空体验也面目全非,发生了紊乱。
那么,自我究竟是什么?W. James写道:一个人的“自我”,按最广义的意义说,是所有他能够称之为“我的”一切之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心理能力,也包括他的衣服住宅,他的妻子和儿女、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牲口,他的游艇和银行账户。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他同样的感情。
这个描述性定义有三点值得重视。一是“我的”,这是“我要” (I will,I need)的产物,也就说的是意志。二是情感,有情便有我,无情便无我,我对我的一切都是有情的,只是不同事物情感强弱不同而已。三是“心理能力”,它跟身体、财产、名誉等一样,都是“我的”所有物,不是自我本身的根本特征。对如此定义的自我的研究也许可以平衡有些人过分强调认知的偏向。
关于自我功能,最好只限于最基本的,即上述定义所描述的情感意志方面,以及对自我的反思领悟、觉察和体验,等。如果把认知功能都扯进来,自我这个概念就会变得很模糊。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局者“迷”显然不是认知能力的问题,而是认知功能暂时被情感意志扰乱了的缘故。荀子谈到人们认知常有所“蔽”,当然也不是认知本身的问题(《荀子.解蔽篇》)。庄子所谓“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齐物论》)说的也是同一道理。
正是从W. James重视情感这个观点出发,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心理社会稳态(psy-chosocial homeostasis)学说按情感强弱的程度将自我分为若干层次,笔者把它简化为三层,外层是利害关系,中层是角色关系,核心是亲密关系。可以说神经症和病理的反应都是自我的核心在成长中有缺陷或成年后发生了变故。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自我核心保持充实而稳定,角色和利害关系即使大变,也不会出现精神障碍。自我核心的内容可以是某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如夫妻、亲子等),也可以是个人最高价值和理想(因人而异,如生命、财产、信誉、社会地位、权力、良心、信仰,等)。这一学说对理解神经症一类的精神障碍和精神卫生都很有意义。三个层次的内容相对稳定,而在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却可以流动,是心理健康的特点。所谓感到空虚或无聊,实际上是核心的内容缺乏;核心里有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内容是神经症性心理冲突的常见情况;在与妻子的关系进入核心而与母亲的关系将被排挤到角色层的时候,年轻的男人会感到十分尴尬和苦恼,如此等等。
2 、自我精神病学
从上述关于自我一般而粗浅的讨论就不难看出自我在精神病学中的重要性。遗憾的是,自我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被忽视了。就重视与否这一点而言,人格与自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有必要在精神病学里划分一个“特区”--自我精神病学,以自我为视角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精神病学。歇斯底里性分离障碍长期被命名为双重人格、交替人格等,其实,这并非人格本身的变化,而是自我的一个方面,即自我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身份)发生了障碍。所谓人格解体,实际上是自我真实感的障碍。过去有一位这个症状的病人自称“无我感”,显得比精神病学教科书术语高明许多。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表明人们只知有人格而自我却被忽视。
以妄想为例。
1985年,笔者曾对妄想作出如下的描述性定义:“妄想是一种个人所独有的和与自我有切身关系的坚信,它不接受事实和理性的纠正。”其中“与自我有切身关系”这一特征主要是引用文献。最近这些年来,精神分裂症前驱期(指出现了精神异常但还没有足以诊断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时期)的自我异常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研究趋向。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或者提供了相当理由使我们推断,妄想的原发性障碍是自我异常。自我体验的异常改变对一个人的心理具有颠覆性,它引起了心理紊乱和严重的不安,这就导致妄想观念(delusional notion)的形成和坚信之稳态复归。
临床观察早已发现,在明确的妄想观念出现前常出现妄想情绪、妄想心境或妄想气氛。这是一种没有明确观念内容的不安和恐惧。这种情绪也没有相应的引发的客观事件,也就是不安和恐惧找不到现实的来源。没有比来源和性质都不清楚的威胁和危险更使人恐惧和难以忍受了。病人遂有解释的必要,这就产生了妄想观念。请比较巫术和神话的起源:当人们对天灾人祸的根源完全无知时,即使荒唐的解释人们也会相信,因为比起什么解释也没有较为令人心安。
K.Jaspers认为,妄想观念是继发的和可以理解的:“病人在晤谈中可以明白告诉我们的妄想内容都是继发性的产物。”
简单而概括地说,妄想结构可以视为由三层组成。其内核是自我异常和它伴随的妄想情绪,第二层次为妄想观念,这是继发性的思维加工,最外一层是病人的言语和行为。这里,所谓结构指一个症状的组成部分以及他们在发生上的关系。
很明显,妄想观念具有代自我(deputed self)的性质。就像一个国家行政首脑的临时代理人一样,他即使不具有远见卓识,没有长远规划,甚至还不时发表自相矛盾的政策演说,却可以使政府维持正常的运转而社会不致陷于无政府状态。通常,妄想的代自我作用是明显的,它维系着相对正常的日常心理和行为,阴性症状和瓦解症状都不明显。在精神分裂症几个公认的临床类型中,妄想型的精神症状瓦解是最不显眼的。也许,除妄想及与它密切相联系的少数几个症状外,家属并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异常。这不能不使人惊叹。妄想观念作为代自我对维系自我的统一和积极性起着多么大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自我,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病人的世界(尤其是病人心目中的他人)也有相应变化的缘故。虚无妄想者不仅认为自己(心灵和肉体)已经不存在,世界也已到了末日。被害妄想充分发展的情况表现为“假社团”(Pseudocommunity),对此,N.Cameron写道“假社团是个想像的组织,它由现实的和想像的若干人组成,而其目的则在于加害病人。”
妄想的原发和继发这两方面的区分,具有临床上的重要性,不仅涉及诊断分型和治疗,也涉及对预后的评估。真性妄想(genuine delusion)有其原发性疾病过程作为根源或基础。所以,即使妄想消失,也并不意味着康复而往往出现缺陷综合征,即情感意志的衰退。与此处于另一极端的超价观念,是人格发展偏离的表现,并非疾病过程所致。所以,它即使持续存在数十年也不出现缺陷综合征。
不妨借用一下精神分析的自我强度(ego-strength)这个概念来加强理解。自我强度指的主要是心理的整合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自我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是接受精神分析的一个必要条件,否则,当分析触及病人的痛点时,病人会出现情绪暴发(如大哭不止)甚至短暂的精神病性反应,从而迫使分析中断。类似地,妄想的代自我具有足够强度者,对治疗有很大的耐受性,即妄想不易改变,同时妄想对维系自我的统一性和积极性的作用也很强,不出现瓦解症状。这样的病例在临床上不少见。
下面再介绍几个妄想的例子。
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病房里收住过一位男青年,他自称并确信自己是艾森豪威尔(二次大战时曾任盟军统帅,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儿子。对此,人们贴个标签:非血统妄想或夸大妄想也就完事。这是令人遗憾的。作为中国普通家庭的儿子和美国总统的儿子,这两种身份大不相同。如是我们具有身份这个概念(身份是自我的一个方面),并且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去和病人晤谈,如询问身份改变时的体验和发生的时间,以及可能的客观标示等,很可能会得到丰富的精神病学资料。可惜的是年轻医生往往会提出“有什么根据?”“为什么长相跟美国人完全不同?”这些挑战病人体验到信念的问题,当然只会引起病人的冷笑和不屑于回答。再者晤谈还必须抓住时机,如果病程较长且接受了药物治疗,病人很可能会不再能回忆妄想前的体验了。
“文革”时,笔者接受劳动改造(在病房专门打扫卫生),曾经见过两位病人,印象深刻。一位是青年男子,自称已怀孕。有一天上午,他忽然说:“要生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表情十分痛苦,满头大汗。当然,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发生。病人平静下来后,起床就去餐厅吃饭,像无事人一样,但怀孕妄想并不改变。对于这位病人,大夫护士们似乎只是旁观者,甚至在看笑话。如果有一位生过孩子的女医生去和病人亲切交谈,询问有关情况,很可能会使病人将自我体验的异常描述一番。
另一位是某大学自控系的教授,中年男子,确信自己是个“妖精”,长期拒食,因为吃饭都“喂了妖精”,身体已很消瘦。这个妄想当然十分荒唐,但看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不由得十分怜悯。这位病人的自我一定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如果我们具有关于自我的一定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是可以发现“妖精”背后的病理体验的。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到外地某精神病院讲课,该院医生向我介绍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男性,55-56岁,住院已17年,可是从住院到当时,每次问起他的年龄,他都回答“38岁”,那是他起病的年龄。该院医生介绍说,除此以外,记忆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显然,病人的病主要不在记忆能力,而是记忆功能受到了自我体验异常的干扰。很可能在起病时,自我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异常,如病人感到获得了“新生”,或者病后的“我”根本就不是原来的“我”,等。可惜起病当时未曾问及自我体验及其改变经过有关的问题。患病已十多年,早已说不清楚了。
幻觉意味着病人不能将他的心理(主观世界)跟客观现实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是公认的自我功能之一。从心理冲突(自我的内在冲实)为视角,就两个维度(一个是自我强度,即自我整合功能的强弱;一个是对立面互相对话或发生联系与否)对某些情况作一个简单分析并列表如下:
当然,还可以以自我为视角,采用不同维度对各种精神症状和病理状态(综合征)进行比较分析,估计对精神病理学的认识深入会有益处。
目前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制订些规范化的关于自我的精神科检查方法(包括病史采取和晤谈)。所谓规范化方法,包括必须询问和弄清楚的方面或项目(大项目下可以有若干子项目)的内容,检查的几种程序(视情况选用其中之一)。至于对病理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评估则不一定要像现在流行的量表那样规定得那么死板,似乎只要按标准化了的量表做,诊断结论就会自动地由计算机打出,无需医生再动脑子。标准化检查决定诊断的做法是可疑的。
自我精神病学检查涉及的方面或项目,大概至少有以下诸项:
(1)自我的需要,即基本的心理需要。马斯洛归结为三: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被尊重与自尊需要。E.Deci和R.Ryar则认为是胜任(competence)、自主(autonomy)和归属(relat-edness)。笔者认为可以把两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如贫困以致饥寒交迫,被奴役、酷刑等),不少人的需求只剩了“活下去”,而心理需要几乎不见了。我们对此应持理解的态度。
(2)自我防御机制。
(3)身份障碍。
(4)真实感障碍。
(5)自我评价。
(以上主要是有关神经症的)
(6)躯体心理性(somatopsychic)障碍(既见于神经症,也见于心身疾患,还可见于精神分裂症),是自我与身体边界或相互作用的障碍。
(7)存在体验障碍(如虚无妄想、癫痫发作)。
(8)自我连续性和同一性体验障碍。
(9)自我的自主性体验障碍(如被控制感)。
(10)自我统一性障碍(可有客观表现,如言语行为瓦解,也可表现为统一性体验异常)。
(11)自我的边界体验障碍(包括两种不同的情况:随意与不随意活动体验的明确区分或混乱,“我”与“非我”的边界)。
(12)性心理性行为(涉及自我)的异常。
这只是一个肤浅的罗列,既无系统性也不完全,不清楚的地方还很多,值得大家进一步研究。